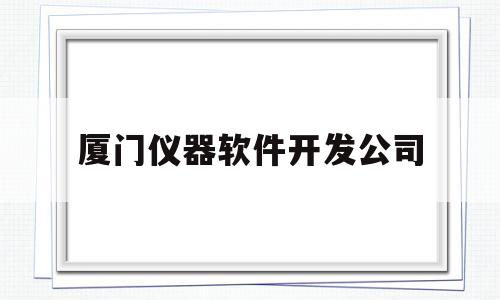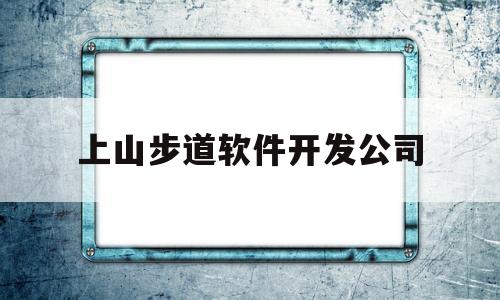历史老师和历史课是中国人了解历史最重要途径之一。如果历史老师把握不住,这个民族就不可能有正确的历史认知与史观。
“什么是历史?”这是扬州中学历史特级教师王雄在高一第一堂历史课上写下的问题。
王雄给学生们提出的问题,也许正是所有历史老师应该给学生们解释清楚的问题。但对于很多历史老师来说,他们更关心的,不是什么是历史,而是学生们的成绩,特别是高考,历史作为文科综合科里一小块残留着。
这是很重要的存在,有了它,历史课才能存在,历史教师才能存在。在我们的网络微调查中,许多人热情地回忆着他们的历史老师,以及历史课给他们带来的快乐。但他们或许没有料到,在更广阔的层面,历史老师和历史课是中国人了解历史最重要途径之一。如果历史老师把握不住,这个民族就不可能有正确的历史认知与史观。
在中国的中小学校里,历史大部分时候不受人待见,就如袁腾飞所言:“历史是副科,在学校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历史学科是平时没人搭理,高考跟你要分。”
某种程度上高考是历史课存在的基础,因为要高考,所以历史课才有存在的价值。有的地方因为中考不考历史,初中就不开历史课,理由是没经费没师资。
打开号称全国文章总量、访问量最大的历史教学网站“中学历史教学园地”,直接冲入眼帘的不是如何提高教学质量、如何吸引学生喜欢历史课的文章,而是各地高考模拟试卷。在这样一个专业网站上,高考依然是最强悍的理由。
在“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中有这样的文字:“通过历史教学,使学生能初步运用唯物史观对社会历史进行观察与思考……;对学生进行国情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教育……具有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和改革开放、振兴中华的使命感……”
这个目标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指向,“唯物史观”、“社会主义”、“国际竞争意识”,这说明历史教育仍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存在,而且犹在培养公民意识和人文素养之上。
而翻开近百年前的民国历史课本——高等小学“共和国教科书新历史”,它的编辑要旨是这样说的:“在使儿童知国家文化之悠久,民族之繁夥。以养成尊重国粹,亲和各族之观念,植中华民国国民之基。”
2006年呼喊多时的历史教材改革,在上海打开了一个小口子。这套高中历史教材出现了瞩目的变化,淡化毛泽东、抗日、起义、革命等内容,更多谈及中华文明、中国文化。
一年后,这版教材被紧急叫停,李文海、沙健孙、张海鹏等7位北京历史学家对这本教材提出批评意见,结论认为:“编撰者思想混乱,使该教科书既脱离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也脱离中国史学发展的实际,‘淡化意识形态’、‘非意识形态化’的表现比比皆是。”
樊树志
我一生都无法追上的历史老师
1957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樊树志,列出的老师清单羡煞旁人——周谷城、陈守实、周予同、谭其骧。若是一个个请出来坐坐,就是一幅“民国范儿”。
忆起学生时代的历史老师,明史大家樊树志如数家珍:“我很幸运,能成为大师们的弟子,现在的学生没有这样的福气了。”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周谷城、陈守实、周予同、谭其骧等史学大家立在前面,成为他一生追寻的目标。
周谷城——仪表永远庄重
让樊树志印象最深的老师当属名气最大的周谷城:“他一个人完成《世界通史》与《中国通史》,在中国历史学界既能写世界通史,又能写中国通史的人,就他一个。”身为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周谷城与毛泽东关系密切,两人曾于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共事,随即建立了私交。在樊树志的印象中,这位当年名声盛隆的周教授上课从不讲究技巧,在那个没有教材没有课本的年代,他仅靠着一纸讲稿挥洒自如。“一堂课45分钟,他先念35分钟的讲稿,我们跟着做笔记,剩下10分钟他就开始聊自己经历中有意思的事情。”那些与毛泽东之间的交往故事。
如今同样身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的樊树志,在课堂上常年保持注重仪表的习惯,“能穿西装就穿西装,天气热的时候就短袖衬衫,但一定要配领带”,如此严谨的态度正是师承自周谷城。上世纪50年代全国人民生活水平普遍偏低,一身布料中山装几乎可算最高配置,但周谷城始终不改西装革履的习惯,对他而言,庄重的仪表意味着对课堂和人生的毫不含糊。
周予同——能抄一面漂亮的黑板书
在没有教材的课堂上,另一位老师周予同选择了比念讲稿更吃力的方式——写板书,一列列的竖写繁体字漂亮而整洁。书香在充满韵味的书写中悠然而至,同学们一边陶醉地欣赏,一边忙不迭地抄写,甚至暗自庆幸老师有写板书的习惯,因为他那带温州口音的普通话,常让人误把“班固”听成“苞谷”……多年后当樊树志也开始在黑板上书写时,“才知道写板书有多累”。老一辈教授的魅力如老酒般徐徐散发,看似书呆子的周老师不仅有趣,还深知调节气氛的法门,总是在学生们奋力抄写板书的空隙,看似随意地聊聊文坛逸事,轻易撩起小年轻的热情。“解放前,周老师在著名的开明书店担任编辑,叶圣陶、郑振铎这些文化名人都是他的同事。”
陈守实——讽刺同辈学者毫不留情
要说直接影响到樊树志人生走向的,莫过于清华国学研究院出身的陈守实老师。师承自梁启超与陈寅恪的陈守实,深受梁启超的史观影响,研史过程中始终坚持要有自己的见解,总在课堂上拿出许多和学术界流行观点截然不同的新史观。
“当时流行说中国古代农村土地是国有的,但他坚决反对这种说法,认为自秦汉以来中国农村土地都是私有的。”陈老师肚子里有货,惯持一股子知识分子式的高傲,当着学生的面讽刺同辈学者简直就是不可或缺的常事。
也是这样一位老师,在看过樊树志论述明清漕运的本科论文后,晚上突然出现在男生宿舍:“哪一位是樊树志?你的论文写得很好嘛!”这对樊树志产生的激励作用无可言喻,不久这篇论文发表在上海的学术期刊上,这对本科生而言是莫大的荣誉。“后来我留校任教,专职从事明清史的研究,一步一步,都离不开陈老师的影响。”
一群遵持传统文化态度与习惯的老师早已离世,樊树志对师生差距有着难以弥合的羞愧:“留洋回来的精通外文,留在本土的精通国学。”也是一种对同辈人成长于艰难环境的怜惜:“我1957年进复旦,遇上反右运动,大跃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64年以后搞四清运动,又把老师学生弄到农村去,直到文化大革命,完全停课。80年代我们就使劲儿补,但终究还是赶不上。这一代的佼佼者几乎都是拼命拼出来的。”
樊树志想起自己那位少年成名的谭其骧老师,能穷毕生心血著就《中国历史地图集》,完全因为这是毛主席布置的任务,中央高度重视,所以能保证研究过程不受政治运动的干扰,但“其他人没有这个条件,说不定哪天就被下放到农村去了”。(文/孙雅兰)
樊树志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明清史专家,代表作:《晚明史》、《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
傅国涌
教育不应只追求成功
“不追求成功,而追求成全人”的教育,是傅国涌心中的理想教育,他希望“教与学都充满开放性、不确定性、愉悦性,学生、老师相互成全,各自找到人生自我实现的方式”。
对于傅国涌来说,“历史”早已是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日常简单的慢生活中,他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读史料,思考中国百年来的命运沉浮,“我就活在历史当中,也以历史为业”。
不太为公众所知的是,这位当下中国颇具影响力的民间历史学者,在早年亦曾有过短暂的乡村中学教师的经历。1987年9月到1989年1月,20岁出头的傅国涌在浙江温州任教,担任语文和历史老师。这段经历让傅国涌有机会深切感受到20年来中学历史教育的“变”与“不变”——形式上变化很大,课本华丽了,教学更花里胡哨了,但本质上,仍然是按照政治标准而不是教育本身来进行的。
彼时,在傅国涌的历史课堂上,虽然仍是按照教材的脉络,但并没有照本宣科。注重史料的他,以讲史实为主,将大篇幅的讲述放在了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上,以更宽的人文视野引导学生去探寻历史的真相。多年以后,当傅国涌再次与当年的学生聚首时,对于当年的授课,不少学生都直言“受益匪浅”。
在傅国涌的印象中,那时的学生还很淳朴,不急功近利,有着对知识纯粹的渴望。到了今天,整个时代已经变得非常功利,许多人读书精于算计,义无反顾地奔着实用的东西去,有着明显的功利性,人成了考试的机器,而历史并不能带来直接的利益。“在重应用、重技术的时代潮流中,历史是一门边缘化的学科,包括历史在内的整个人文学科都不被关注和重视,这是教育制度设计和整个社会环境导致的。”
近年来,傅国涌不时会到一些中学讲学交流,在与各地学生的接触中,他发现,一方面,有些学生对历史的了解比他想象的要深入很多;另一方面,有的学生所提的问题会让他啼笑皆非,“他们问的只是后面的部分,却并不知道前提是什么”。
“总体而言,现在仍然是人文匮乏的时代,在我们这个有着很深的历史传统的国家中,现在的人们不了解历史,大部分资讯来自零碎的片段的大众媒体,比如讲求娱乐化的电视,它是要好玩的有趣的,这就与准确、客观、完整相背离。大部分人还没有形成建立在历史事实上的健全价值观。”在傅国涌看来,在随波逐流中,只有极少数人能跳出来,远离封闭的精神状态。
在中国,成功成了一种毒药,它被功利地定义成了“做大官发大财”,而教育有它本身的逻辑和规律,只有回到教育自身,从它自身出发,而不是从它以外的“成功”出发,教育才真正实现了“教化育人”的作用。
说到“读书过程中无意的副产品”,傅国涌自己就经历过不少。在长期读史料的过程中,傅国涌无意中接触了很多人对过去中小学的回忆,他由此汇编了后来引起教育界和新闻界关注的《过去的中学》、《过去的小学》。这两本反映晚清到民国50年间中小学教育的著作,通过整理大量回忆录,借由几十位过去的校长、老师、学生之口,其中不乏胡适、赵元任、钱穆等名家大师,打捞过去鲜活的中小学记忆,进一步体认那个时代的中小学教育。
“那个时代的教育也有它的问题和缺点,但它最大的特点是始终围绕着人的教育,而不是工具的教育,它是以人的健全为目标的。它是成全人的教育,而不是成功的教育。这种人的教育,是那个时代的教育呈现出来的最有生命力的一个侧面。”这种“不追求成功,而追求成全人”的教育,是傅国涌心中的理想教育,他希望“教与学都充满开放性、不确定性、愉悦性,学生、老师相互成全,各自找到人生自我实现的方式”。 (文/郭小为)
傅国涌历史学者,曾任中学历史教师,代表作:《金庸传》、《1949: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
袁腾飞
如何让学生对历史感兴趣?他做到了
“中学历史教材最大的不足,在于它的语言成人化,只讲概念不讲故事,味同嚼蜡。”
成名后的袁腾飞从来坚决否认自己是公共知识分子,他给自己定位为一名普通的中学历史老师。对于“史上最牛中学历史教师”的称号,他总表示“愧不敢当”,“北京2500个中学历史教师,很多很优秀”。
在他眼里:“优秀的历史老师必定能够启发学习兴趣,通过他的历史课会让学生对这门课产生浓厚的兴趣,下课之后愿意去翻翻教材以外的历史书籍,并对历史现象有自己的思考。”
“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历史课。
袁腾飞生于1972年,在中学连个组长都没当过。大学毕业时,他特别犹豫要不要当历史老师,“当时教师的待遇很低,家有隔夜粮,不当孩子王”。同时他又烦考据,不想加入传统的史学圈。于是,他在据说是重点学校的首都师范大学附中教了15年,后调入北京海淀进修学校。
袁腾飞碰上了读书无用论最猖獗的时候,那时人们认为会外语、会电脑、会开车,这就属于人才。“何况历史是副科,在学校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
如果他按部就班地讲课,一定会乱堂,最终,那些冷落他的学生给了他启迪。一次,课堂上他讲到林则徐虎门销烟,他说在海边挖池子,海水引进来,投进石灰和鸦片搅拌,起化学反应后,残渣排进大海,学生们在下边大喊:“老师,林则徐不环保。”此后“林则徐不环保”也成了他的包袱。
从此,他开始了这种嬉笑怒骂的风格,学生们也确实喜欢。上历史课前昏昏欲睡的学生会精神奕奕,聆听这位八字腿、黑眼镜老师的课,一些理科生和老师也经常旁听。
袁腾飞成了首都师范大学附中最受欢迎的教师之一,不仅是海淀区历史学科的带头人,也为高考命题,编写教材。首都师范大学附中的校长石彦伦曾撰文研究袁腾飞的教学方法,“讲得生动、丰富、灵活,效果理想”。
有一部分人认为袁腾飞哗众取宠。不过支持他的人也不少,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曾表示:“说他思想混乱根本就是不存在的问题,教育不可能给学生建立一个‘花园’,必须告诉学生,这里有花有草,还有刺。”作为一名中学历史老师,如何让学生对历史感兴趣是很重要的,而袁腾飞做到了这一点。
“你站在什么阶级的立场上说话呢?”
谈起他所经历的历史课堂,袁腾飞几乎没太多能回忆的细节。“和一般人经历的没有什么区别。”他喜欢历史,是受到评书演艺和京剧的影响,而学校的历史课并没有激发他多少兴趣。
20岁的时候,袁腾飞曾经问过一位大学老师:“马克思主义五种社会形态,太平天国属于哪种?”老师说:“属于封建政权。”袁腾飞说:“太平天国是封建政权,清朝也是封建政权,俩封建政权,为什么太平天国就是正义的,清朝就是落后的?”
老师斜斜瞥了袁腾飞一眼,问:“你站在什么阶级的立场上说话呢?”
他后来幸运地遇到了首都师范大学教授于友西。于友西在袁腾飞彷徨失落时,一直鼓励他发挥个人特长并支持他创新。袁腾飞告诉《新周刊》记者:“没有这位恩师的点拨,就没有我的今天。”
2007年起,袁腾飞被调入北京海淀教师进修学校任历史学科研究员。他观察发现,近二十年来中学历史老师的地位没有丝毫提高。
他说:“不但无法跟数理化外语相比,甚至就连音体美也比不了。音体美没有考试压力还能指导学生竞赛获奖,为学校赢得各种荣誉。这一点历史学科根本无法做到。历史学科是平时没人搭理,高考跟你要分。”
“正史很好看,很有趣,很逗,但教科书不好看。中学历史教材最大的不足在于它语言的成人化,只讲概念不讲故事,味同嚼蜡。”曾断言“历史教科书可以烧了”的袁腾飞已经好些年没登上学校的历史教坛了。前几年他在《百家讲坛》讲得兴致勃勃,近日则忙着录制《腾飞五千年》。非正式的教学舞台上,他不用再关心应试技巧,而是纯粹按自己的兴趣讲故事。 (文/钟瑜婷)
袁腾飞北京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海淀区历史学科带头人,以幽默犀利的语言向学生传授历史知识,被网友奉为“史上最牛中学历史老师”。
李远江
让历史变得有温度、可触碰
他开始尝试更多的历史教学和传播方式;因为相信“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历史的书写者”,他发动更多的人一起来打捞民间历史记忆,从精英史观跳脱到公民史观。
从中学历史老师到历史杂志的编辑记者,再到民间历史公益记录的推动者,李远江的人生轨迹一直与“历史”同行。
他说自己所做的事情很简单,就是尽可能地还原历史;他也坦言这样的工作任重道远,“停不下来,需要更多人的参与”。在“对未来一代人的争夺”中,他开始尝试更多的历史教学和传播方式;因为相信“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历史的书写者”,他发动更多的人一起来打捞民间历史记忆,从精英史观跳脱到公民史观。
一切只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也应该成为自己历史的主人。
对未来一代人的争夺。
李远江笑言自己在学校里是“属于校长不太喜欢的那一类老师”。他敢于多说话,总是试图让学生触摸历史真相。本来,在整个人文学科中,以实证为基础的历史学科最具科学逻辑和科学方法,但表达国家意志的教科书仅仅只是一家之言。作为一位历史老师,李远江说自己所要做的,就是“换一个角度,从普通人的立场,给学生更多不一样的东西”。
这时,李远江担心的问题随之而来——当把非教材需求的观念教给学生时,他们会不会产生一些困扰,会不会引起更多的困惑和反弹?这样的疑惑最终被来自扬州中学的历史老师王雄解答了。
在王雄的课堂上,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对于同一历史事件,既有基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一套表述,也会看到被精选出来的其他立场的历史论述,这时矛盾和冲突就会出现,而学生反而更感兴趣了,他们会想知道为什么不同的人对于同一件事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观点。
提供更多的历史细节,让学生进入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进而产生脑力的激荡和价值观的碰撞,最终使学生的人格趋于健全和理智。在这一套教学思路之下,不少学生都愿意主动参与到这种思维的挑战中来。
曾有四个其他老师眼中的“差学生”的历史读书笔记让李远江印象深刻,“并没有强迫,这些孩子在历史领域找到了自我实现的机会”。
李远江对这种注重学术性和多元性的教学方式很是推崇,他发现,大多数学生最终既不糊涂,也不是某些人想象中的那种“反动”,而是变得更冷静了,他们清醒地知道,历史教材是基于某一政党的利益或视角来看问题,这只是它自己的一种表达。这种冷静所带来的直接结果是,在高考时,学生已经知道将要回答的是什么,“就像面试一样,他们不会再困扰纠结了”。
即便如此,仍有一些“唯成绩至上”的学生,在功利考量和学习压力之下,并不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了解多元的东西,觉得把“高考需要的”学到就行了。“你喂我一口饭就行了,为什么要给我吃一桌菜呢?”
李远江清醒地意识到,在教育观念碰撞最厉害的中学阶段,让刚刚开始形成历史观的青年有机会碰触真实的历史,让他们成为未来的公民,而不是被另一种力量塑造成“螺丝钉”,这样的任务相当艰巨,他说,这是未来的主战场,“我称之为‘对未来一代人的争夺’”。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历史的书写者。
当很多人还纠结于教材问题时,李远江已经意识到,如果按照王雄老师的这一套教学方式,教材本身就会退位,它只是一种参考,不再统辖一切,老师可以把更多元的视角引进来,“所以人是核心的,如果老师没有变的话,换什么样的教材也没用”。
根据李远江的多年观察,在中国只有不到两成的历史老师把历史教学当成事业,“他们有一定的教育理想,希望给孩子们提供一种受益终生的教育模式”。有鉴于此,近两年来,李远江的一大工作重心就是——把这部分有理想但又对现实不满的老师找出来,让他们先动起来,做好领头兵。
为此,李远江和他所服务的北京彩虹公益基金会,开始面向全国的中学历史教师做拓展性的公益培训,让他们跟历史学界最领先的一些学者面对面地交流学习,接触学术前沿。
去年夏天,共有来自北京、广东、广西、贵州、江西、浙江、山西等全国各地的近300名历史老师在北京参加了这样的培训。“当他们的视野被打开的时候,就能把这些新观念新方法带到课堂中去,进而影响学生,最怕的是老师本身视野很狭小,还认为自己做的是正确的事情。”李远江和他的团队计划,在未来5年内培训一万名中学历史老师。
更早之前,李远江就已经开始了这种以切身行动介入社会开展历史教育的实践。2011年,李远江发起组织了“全国中学生历史写作大赛”,号召和鼓励普通中学生书写身边的历史。与以往见到的精英史观不同,在这场“中学生写史”运动中,人们看到的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王侯将相、精英人物的宏大叙事,而是在历史长河中快要被淹没、被牺牲、被遗忘的芸芸众生的鲜活记忆。
这场上万人参与进来的“中学生写史”运动,延续至今,涌现了一大批优秀作品。山东师大附中雷宗兴同学通过调查发现外高祖父并非“汉奸”,而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农学家,卸下了整个家族背负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包袱,“文革”后星散的家族重新走向融合。
东莞中学松山湖学校左馨兰同学追寻外婆在战争年代的漂泊史,用细节还原了抗战全面爆发后十二年的民间历史。
厦门二中郭悯娜引导我们聚焦一个乡村五保户的悲惨命运,引发了社会对农村社保的思考与关注……
“这让历史的记忆变得有温度、可触碰,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历史的书写者。”李远江的努力得到了认可,2013年年初,在由《社会创业家》杂志主办的“首届社创之星评选活动”中,他被推荐为2012年度候选人之一。评委的推荐语是:“李远江的全国中学生历史写作大赛能够引导学生从自我认知的需要出发,按照历史研究的方法去调查研究身边的历史……这正是现代公民社会构建的伦理基础。”
在喝彩声之外,也出现了批评的声音:“这样做会不会制造很多上街的愤青?”李远江的回答坚定而直接——不会。他相信,一个真正懂得历史,学好了历史的人,一定可以多角度换位思考问题,在面对突发状况时,会尽可能去稳定局面,而不是诉诸暴力,这就是历史认知对人的行为方式某种可以预见的改变。 (文/郭小为)历史老师和历史课是中国人了解历史最重要途径之一。如果历史老师把握不住,这个民族就不可能有正确的历史认知与史观。
“什么是历史?”这是扬州中学历史特级教师王雄在高一第一堂历史课上写下的问题。
王雄给学生们提出的问题,也许正是所有历史老师应该给学生们解释清楚的问题。但对于很多历史老师来说,他们更关心的,不是什么是历史,而是学生们的成绩,特别是高考,历史作为文科综合科里一小块残留着。
这是很重要的存在,有了它,历史课才能存在,历史教师才能存在。在我们的网络微调查中,许多人热情地回忆着他们的历史老师,以及历史课给他们带来的快乐。但他们或许没有料到,在更广阔的层面,历史老师和历史课是中国人了解历史最重要途径之一。如果历史老师把握不住,这个民族就不可能有正确的历史认知与史观。
在中国的中小学校里,历史大部分时候不受人待见,就如袁腾飞所言:“历史是副科,在学校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历史学科是平时没人搭理,高考跟你要分。”
某种程度上高考是历史课存在的基础,因为要高考,所以历史课才有存在的价值。有的地方因为中考不考历史,初中就不开历史课,理由是没经费没师资。
打开号称全国文章总量、访问量最大的历史教学网站“中学历史教学园地”,直接冲入眼帘的不是如何提高教学质量、如何吸引学生喜欢历史课的文章,而是各地高考模拟试卷。在这样一个专业网站上,高考依然是最强悍的理由。
在“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中有这样的文字:“通过历史教学,使学生能初步运用唯物史观对社会历史进行观察与思考……;对学生进行国情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教育……具有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和改革开放、振兴中华的使命感……”
这个目标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指向,“唯物史观”、“社会主义”、“国际竞争意识”,这说明历史教育仍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存在,而且犹在培养公民意识和人文素养之上。
而翻开近百年前的民国历史课本——高等小学“共和国教科书新历史”,它的编辑要旨是这样说的:“在使儿童知国家文化之悠久,民族之繁夥。以养成尊重国粹,亲和各族之观念,植中华民国国民之基。”
2006年呼喊多时的历史教材改革,在上海打开了一个小口子。这套高中历史教材出现了瞩目的变化,淡化毛泽东、抗日、起义、革命等内容,更多谈及中华文明、中国文化。
一年后,这版教材被紧急叫停,李文海、沙健孙、张海鹏等7位北京历史学家对这本教材提出批评意见,结论认为:“编撰者思想混乱,使该教科书既脱离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也脱离中国史学发展的实际,‘淡化意识形态’、‘非意识形态化’的表现比比皆是。”
李远江《东方历史评论》高级编辑,全国中学生历史写作大赛总策划,曾任两年中学历史教师。
来源:广东新周刊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