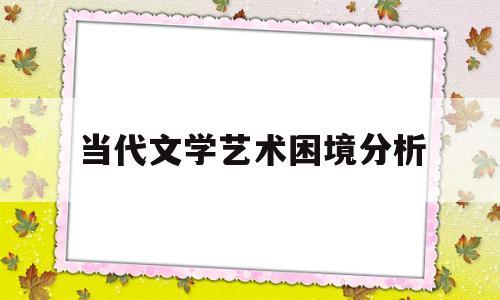本文是受《艺述中国》杂志邀约写的小短文,杂志社的要求是希望讨论一下当代艺术与所谓文人精神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老生常谈的话题,谈这样的话题已经很难透视当前的文化状态了,因此没有太大的写作价值,但要写具体也会很复杂,于是就蜻蜓点水地写了几点,并没有展开,仅在一些比较关键的问题上稍作停留,正所谓点到为止。
——编者按
文人,在中国历史上曾扮演一种社会中间物的角色,有时怀揣政治理想与道德志向,积极参与社会建设,曾发挥过一定作用;有时在庙堂上受挫之后心灰意懒,或心有余悸,有兔死狐悲的心情,于是归隐田园或山林,了却残生,亦或默默等待风起。文人与权力体制若即若离,一只脚在其中,一只脚游离其外 ,游刃有余。虽时有抗命殉道之人,但总体上扮演着和稀泥(调节与缓冲)的角色。近代以来,中国遭遇现代性,文人的浪漫之梦算走到尽头,稍有头脑和道义的士人皆意识到,必须向西方学习,哪怕他们再不情愿,这是一个大部分国人都极力掩盖的基本事实,即:若果我们不是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步,也不会在整个20世纪都积极拥抱现代性及其文化。其实明眼人都明白,他们学习的不是西方,而是一个叫做“现代”的整体性社会方案,而且这方案自身就具有自我批判的功能。
李老十 文章何处哭秋风 设色纸本
文革中知识分子被批斗的典型场面
改革开放以后,向西方学习伴随着“解放思想”一起,使中国社会文化重新焕发活力,一部分人们再也不留恋“文人”的矫情与自恋,日以继夜地学习、吸收、改造现代文化诸般成果,以期待将这些努力为当代中国走向现代尽一份力。另一部分文人或模模糊糊,或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或下意识、或刻意地重新捡起 “文人”和“传统”的招牌,一茬一茬“国学大师”、“新文人画家”、“气功兼武学宗师”等神棍粉墨登场。传统的回归,并不意味着古典学术的重建,而更多体现为某种漠视现实问题的思潮在兴起、壮大。当代的文人意识进一步蜕变,不再具有曾经本就不多的道义与持守,也基本丧失了对社会民生的热心与责任感,沦为一种随意可以挪用、阐述、定义的符号。以至于现在碰到一位以“文人”自居的人物,基本皆可以断定其为骗子或恶棍。文人意识已经无法对当代文化提供什么有活力的新贡献,反而成为维护权力体制、粉饰现实裂痕的工具,其吸引力不减,更说明社会思想危机之深。与文人路向不同的那一批人在80年代就自觉成为“知识分子”,经历了80年代末的风波和90年代初的市场大潮连续洗礼,大部分人也基本放弃了曾经的立场与态度,转变为靠知识吃饭的食客。真正的知识分子,除了拥有自己在知识、理论、思想方面的个人系统及专业能力之外,更重要的是有一颗紧贴时代处境的敏感心灵,以及敢于对现实诸般问题进行独立分析与批判的胆识。若以此观之,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简直少得可怜,甚至这个群体是否尚存都成了一个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曾经的西单民主墙盛况
朱新建《金瓶梅画页》 设色纸本
知识人的集体沉默、知识分子的功能缺失,让我们不禁对当代思想文化所处的社会环境产生无尽的遐想。知识分子的困境除了来自传统伦理的招安、体制利益的诱惑、个体信念的坍塌这些原因之外,也来自对存在本身的担忧。政治学的逼仄感,这是一个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体验,谁都知道有一些框架是碰不得的。知识分子,常以反思为长处、以行动为短处,反思落到纸上或许还愿动动手腕,当他们看到行动潜在的困难之后,大部分人不仅会望而却步,有时还会因此而自我审查,这样一来就加剧了整个知识界、学术界的进一步“学术化”(其实就是“去问题化”和“去政治化”),于是各大教育和研究机构(包括从事艺术活动的美术馆)都不可避免地背对时代关键性问题,整体上走向平庸与衰败。一切都那么平静,平静得意味深长。
秦晖与汪晖代表的两种倾向与诉求的知识分子之间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博弈
重新激活思想家、知识人和艺术家的思想、创作活力,只能落实在每个个体自身的行动上面。这是一种在特殊语境下的“再启蒙”运动,是微观的启蒙,主要是“启蒙”自己,同时或多或少地“启蒙”一下身边的个体。这也是在一片瓦砾中,以“愚公移山”的方式来重新奠定现代性的工作,荒诞的是,现代性方案的再启动居然在当代还如此紧迫。
2016/11/27 于清华园
欢迎订阅公众号“不周山”:buzhoushan54321